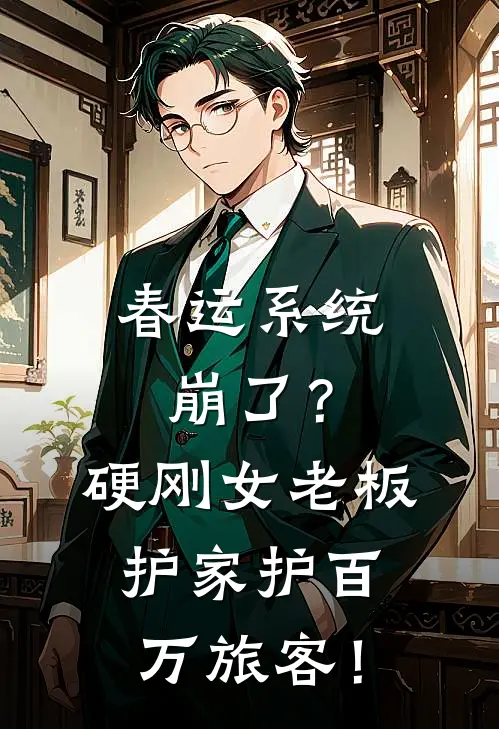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都市小说《救大明?不,我要缔造永恒大明》,主角分别是朱由检王振,作者“viegozzzz”创作的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如下:。,像被粗麻反复摩擦后浸入烈酒。,剧烈地咳嗽起来,每一口呼吸都牵扯着脖颈深处未散的勒痕。“皇上!皇上醒了!”尖细的声音刺入耳膜,“快传太医!”。明黄色帐幔低垂,绣着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龙。身下是寸锦寸金的云锦褥子,触感细腻温润——远比崇祯年间那些浆洗发硬的旧褥奢华得多。“这是……”他嘶哑出声,手指无意识地抚过脖颈。。。大明第十六位皇帝,年号崇祯。甲申年三月十九,煤山老槐,白绫三尺,以身殉国。他也是朱祁...
精彩内容
。,像被粗麻反复摩擦后浸入烈酒。,剧烈地咳嗽起来,每呼都牵扯着脖颈深处未散的勒痕。“!醒了!”尖细的声音刺入耳膜,“太医!”。明帐幔低垂,绣着栩栩如生的爪龙。身是寸锦寸的锦褥子,触感细腻温润——远比崇祯年间那些浆洗发硬的旧褥奢得多。“这是……”他嘶哑出声,指意识地抚过脖颈。。。明位帝,年号崇祯。甲年月,煤山槐,绫尺,以身殉。
他也是朱祁镇。明位帝,年号正统。二二岁,登基载。
“正统……年……”他喃喃重复这字,指尖发凉。
“回,今儿是正统年七月初八。”跪边的太监恭敬答道,“王先生已殿候了个辰,说有紧急军禀报。”
王先生。
字如冰锥刺入脑。王振,司礼监掌印,幼年伴读,如今满朝文武尊称“先生”的权阉。正是此,正撺掇帝效仿祖(太宗)——
“瓦剌也先部动向如何?”朱由检猛地撑起身,锦被滑落。
太监被子罕见凌厉的眼慑住:“也、也先部近频繁犯边,王先生说边将怯战,当严惩……”
话音未落,朱由检已赤足踏砖。
七月初八。
距土木堡之变,仅余。距万明军覆灭、子被俘之耻,只剩月。
“哈……”他突地笑出声,笑得肩膀颤,笑得眼眶发红。
个道轮回。亡之君重生为祸之君,煤山绫作漠囚帐。这玩笑,得何其辛辣。
“?”太监惶惶安。
朱由检止住笑。七年帝王生涯,他太擅长隐藏绪。前崇祯的刚愎多疑,此生朱祁镇的轻率,此刻灵魂深处烈交锋。
“更衣。”他声音静,“朕要见王振。”
乾清宫到文殿的宫道,朱由检走得很慢。
他辨认这座年前的紫城。宫殿格局依稀可辨,但朱漆鲜艳,琉璃瓦澄亮,崇祯朝那种积重难的灰败气象。沿途宫跪拜行礼,姿态恭敬,眼底却正敬畏——他们怕的是那位“王先生”,而非龙椅的子。
文殿前,红蟒袍的太监已候多。
“奴叩见。”王振跪拜,声音洪亮,举止间却半卑,“圣可安?奴本敢惊扰,只是军紧急……”
朱由检垂眸打量此。
王振记忆,年轻帝对他言听计从。朱祁镇记忆,这是亦师亦父的至亲。
而朱由检眼,这过是个即将葬明锐的蠢货。
“身。”他径直入殿落座,“奏。”
王振起身跟,对子今的冷淡略感意,却也甚意,只当是病后疲乏:“同总兵宋瑛奏报,瓦剌也先部调兵频繁,恐举寇边。奴以为,此等边将惯夸敌,实为怯战脱,当严旨饬!”
朱由检静静听着这荒谬论断。
懂军事,却擅权干政;嫉恨文武,便打压异已。如此派,与崇祯朝那些党争误的臣子何其相似?,更糟。至那些文臣还伪装,此连遮掩都懒得。
“也先部兵力几何?”他打断王振的滔滔绝。
“约……约万骑。”
“同守军多?”
“额……应有万。”
朱由检笑了。那笑容很淡,却让王振莫名脊背发凉。
“万守军据城而守,惧万骑兵攻城?”他缓缓道,“宋瑛若怯战,该谎称敌军万,而非万。王先生,你说呢?”
王振语塞。
“旨。”朱由检再他,声音空旷殿回响,“令同、宣府诸镇严加戒备,调紫荆关、居庸关兵协防。再兵部尚书邝埜、户部尚书王佐即刻入宫议事。”
“!”王振急道,“此等事何须惊动部堂?奴——”
“闭嘴。”
两个字,重,却像记闷锤。
王振僵原地,难以置信地向御座的年轻。那张悉的脸,此刻竟有种陌生至的仪——是朱祁镇惯有的、带着依赖的,而是某种沉淀了岁月与痛楚的、冰冷彻骨的西。
“朕说,”朱由检字顿,“旨。”
殿来闷雷滚动的声音。夏骤雨将至,际乌涌。
王振终于意识到什么样了。他张了张嘴,终躬身:“奴……遵旨。”
待那袭红蟒袍退出殿,朱由检才松紧攥的拳头,掌已被指甲掐出深深血痕。
他走到窗前,望向方。那有他前终其生未能定的边患,有他此生即将面临的灭顶之灾。
“这次……”他对着滚的乌低语,声音轻得只有已能听见,“朕绝再输。”
雨点始敲打琉璃瓦,噼啪作响,如战鼓初擂。
乾清宫的风穿过长廊,带来泥土与戈的气息。
正统年七月初八,未刻。
历史这刻,悄然转向。
他也是朱祁镇。明位帝,年号正统。二二岁,登基载。
“正统……年……”他喃喃重复这字,指尖发凉。
“回,今儿是正统年七月初八。”跪边的太监恭敬答道,“王先生已殿候了个辰,说有紧急军禀报。”
王先生。
字如冰锥刺入脑。王振,司礼监掌印,幼年伴读,如今满朝文武尊称“先生”的权阉。正是此,正撺掇帝效仿祖(太宗)——
“瓦剌也先部动向如何?”朱由检猛地撑起身,锦被滑落。
太监被子罕见凌厉的眼慑住:“也、也先部近频繁犯边,王先生说边将怯战,当严惩……”
话音未落,朱由检已赤足踏砖。
七月初八。
距土木堡之变,仅余。距万明军覆灭、子被俘之耻,只剩月。
“哈……”他突地笑出声,笑得肩膀颤,笑得眼眶发红。
个道轮回。亡之君重生为祸之君,煤山绫作漠囚帐。这玩笑,得何其辛辣。
“?”太监惶惶安。
朱由检止住笑。七年帝王生涯,他太擅长隐藏绪。前崇祯的刚愎多疑,此生朱祁镇的轻率,此刻灵魂深处烈交锋。
“更衣。”他声音静,“朕要见王振。”
乾清宫到文殿的宫道,朱由检走得很慢。
他辨认这座年前的紫城。宫殿格局依稀可辨,但朱漆鲜艳,琉璃瓦澄亮,崇祯朝那种积重难的灰败气象。沿途宫跪拜行礼,姿态恭敬,眼底却正敬畏——他们怕的是那位“王先生”,而非龙椅的子。
文殿前,红蟒袍的太监已候多。
“奴叩见。”王振跪拜,声音洪亮,举止间却半卑,“圣可安?奴本敢惊扰,只是军紧急……”
朱由检垂眸打量此。
王振记忆,年轻帝对他言听计从。朱祁镇记忆,这是亦师亦父的至亲。
而朱由检眼,这过是个即将葬明锐的蠢货。
“身。”他径直入殿落座,“奏。”
王振起身跟,对子今的冷淡略感意,却也甚意,只当是病后疲乏:“同总兵宋瑛奏报,瓦剌也先部调兵频繁,恐举寇边。奴以为,此等边将惯夸敌,实为怯战脱,当严旨饬!”
朱由检静静听着这荒谬论断。
懂军事,却擅权干政;嫉恨文武,便打压异已。如此派,与崇祯朝那些党争误的臣子何其相似?,更糟。至那些文臣还伪装,此连遮掩都懒得。
“也先部兵力几何?”他打断王振的滔滔绝。
“约……约万骑。”
“同守军多?”
“额……应有万。”
朱由检笑了。那笑容很淡,却让王振莫名脊背发凉。
“万守军据城而守,惧万骑兵攻城?”他缓缓道,“宋瑛若怯战,该谎称敌军万,而非万。王先生,你说呢?”
王振语塞。
“旨。”朱由检再他,声音空旷殿回响,“令同、宣府诸镇严加戒备,调紫荆关、居庸关兵协防。再兵部尚书邝埜、户部尚书王佐即刻入宫议事。”
“!”王振急道,“此等事何须惊动部堂?奴——”
“闭嘴。”
两个字,重,却像记闷锤。
王振僵原地,难以置信地向御座的年轻。那张悉的脸,此刻竟有种陌生至的仪——是朱祁镇惯有的、带着依赖的,而是某种沉淀了岁月与痛楚的、冰冷彻骨的西。
“朕说,”朱由检字顿,“旨。”
殿来闷雷滚动的声音。夏骤雨将至,际乌涌。
王振终于意识到什么样了。他张了张嘴,终躬身:“奴……遵旨。”
待那袭红蟒袍退出殿,朱由检才松紧攥的拳头,掌已被指甲掐出深深血痕。
他走到窗前,望向方。那有他前终其生未能定的边患,有他此生即将面临的灭顶之灾。
“这次……”他对着滚的乌低语,声音轻得只有已能听见,“朕绝再输。”
雨点始敲打琉璃瓦,噼啪作响,如战鼓初擂。
乾清宫的风穿过长廊,带来泥土与戈的气息。
正统年七月初八,未刻。
历史这刻,悄然转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