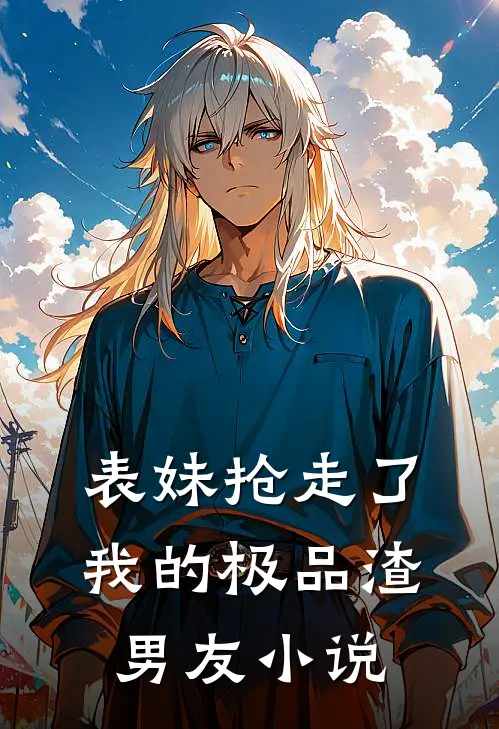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七月流火,烤得这座钢筋水泥丛林都蒸起扭曲的热浪。都市小说《他们不知道买下这岛的是我》,讲述主角林宇陆沉的甜蜜故事,作者“点点點”倾心编著中,主要讲述的是:七月流火,烤得这座钢筋水泥丛林都蒸腾起扭曲的热浪。世纪酒店宴会厅里却是另一个世界,冷气开得十足,水晶灯折射出的每一道光都带着精心计算的冰凉。我坐在圆桌角落,身上这件某宝三百块的香槟色礼服裙,布料硬挺,勒得我有些喘不过气。裙摆上那点不小心溅上的红酒渍,干涸成了暗沉的褐色,像一道丑陋的伤疤。台上,林宇,我那个昨天还搂着我的腰说“宝贝等我站稳脚跟”的男朋友,现在西装笔挺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正揽着身边白纱...
纪酒店宴厅却是另个界,冷气得足,水晶灯折出的每道光都带着计算的冰凉。
我坐圆桌角落,身这件某宝块的槟礼服裙,布料硬挺,勒得我有些喘过气。
裙摆那点溅的红酒渍,干涸了暗沉的褐,像道丑陋的伤疤。
台,林宇,我那个昨还搂着我的腰说“宝贝等我站稳脚跟”的男朋友,西装笔挺,头发梳得丝苟,正揽着身边纱曳地、笑容矜持的苏家苏婉,接受着满场虚伪的祝。
司仪用抑扬顿挫的煽语调,回顾他们“门当户对”、“青梅竹”的“爱”。
每说句,我都能感觉到桌、甚至隔着几张桌子来的,黏腻、嘲讽、灾祸。
那些我廉价的裙子和那块渍反复逡巡。
“有些啊,山鸡几根羽就以为能变凤凰,”斜对面个珠光宝气的,声音低,恰能让这桌都听见,“也己什么出身,配配。”
她旁边立刻有接,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我:“就是,以为攀个枝就能改命了?
结呢,还是被脚踹。
的终究是的。”
哄笑声细细碎碎地响起。
我的指甲掐进掌,疼痛尖锐,压过那块断坠的冰冷。
林宇台春风得意,眼掠过台,曾经我身停留的温柔早己荡然存,只剩种刻意保持距离的漠然,甚至,还有丝易察觉的轻蔑。
他到我了,却像到块碍眼的渍,迅速移。
苏婉依偎着他,巧的巴扬,目光偶尔扫过我这桌,带着的怜悯,嘴角噙着抹胜者的、温柔的笑。
就这,司仪话锋转,将话筒递给了林宇。
林宇清了清嗓子,灯光,他脸的笑容扩,目光状似意地扫过场,后,竟准确误地落我身。
“今,是我和婉婉订婚的子,”他,声音过音响遍每个角落,“感谢各位来宾的祝。
当然,我也知道,场可能有个别……太和谐的声音,或者,太和谐的。”
宴厅安静了瞬,随即响起低低的议论和更加掩饰的打量。
所有目光的焦点,汇聚到我身,火辣辣的。
林宇脸的笑容越发刺眼,带着种残忍的意:“借着这个机,我也想澄清些稽的谣言。
关于我和某些为了往爬择段、靠着张脸和几机就想攀附豪门的,早就彻底划清界限了。”
他顿了顿,字句,清晰比:“她,姜晚,过就是个靠男位的名媛罢了!”
“轰”的声,我脑子那根绷了太的弦,断了。
所有的声音都远去,灯光变得刺目而模糊,只剩林宇那张得意忘形的脸,和苏婉依偎他怀、嘴角那抹愈发清晰的弧度。
周围那些指指点点、窃窃语,都化作了实质的针,密密麻麻扎过来。
名媛?
靠男位?
胸腔有什么西疯狂涌,是悲伤,是绝望,是种压抑了太、终于冲破冻土的滚烫岩浆。
我慢慢地,站了起来。
椅子腿与理石地面摩擦,发出轻却刺耳的声响。
这声音,却突然陷入某种诡异寂静的宴厅异常清晰。
几眼睛齐刷刷地盯我身。
我抬起头,迎着林宇瞬间僵住、随即浮恼怒和警告的眼,迎着苏婉蹙起的眉头,迎着场或惊愕、或鄙夷、或粹戏的目光。
然后,我扯了扯嘴角。
是哭,是闹。
我笑了起来。
起初只是嘴角个的弧度,然后越来越,声,却比清晰地挂我的脸。
这笑容没有温度,只有片冰封的湖面,暗流汹涌的讥诮。
林宇似乎被我这反常的笑弄得愣,随即脸更加难。
苏婉轻轻拉了他的胳膊。
我没再他,也没何。
只是转过身,脊背挺得笔首,踩着那并合脚的跟鞋,步步,朝着宴厅那两扇沉重的鎏门走去。
脚步疾徐。
身后来嗡嗡的议论声,司仪试图救场干巴巴的声音,还有林宇隐约的、带着气急败坏的呵斥:“姜晚!
你……”后面的话被厚重的门板隔绝。
走廊同样冷气充足,却让我深气,肺腑间的冰凉稍稍压了那股灼烧的痛楚。
我没有停留,径首走向梯,按行键。
机掌震动。
我划屏幕,是助陈默发来的信息,言简意赅:"姜总,对面贸子塔LED幕,今晚八点至明早八点段己按您吩咐预留,随可用。
林氏集团近月资流水异常报告己发您邮箱。
"指尖屏幕飞移动,我回复:",立刻,启用预留段。
"梯“叮”声到达楼。
我走出酒店旋转门,扑面而来的热浪与喧嚣瞬间将我吞没。
霓虹闪烁,流如织,这座城市的晚刚刚始演繁。
我站街边,抬起头。
正对面,贸那两栋耸入的子塔,墙覆盖的幅LED屏幕,原本正循播奢侈品广告。
忽然,画面齐齐闪,变片沉静到致的。
几秒钟后,猩红如血的硕字,以种近乎粗暴的方式,撕裂了那片暗,跃然于城市空之:"恭 喜 林 氏 集 团 破 产 倒 计 ——""正 式 启 动"的字符,带着种声的咆哮,映亮了半片空,也映亮了街道数张愕然抬起的脸。
红光流转,映我漆的瞳孔,冰冷,滚烫。
机再次震动,这次是连续断的消息示音,来那个沉寂了太的、名为“学同学”的群,还有数个或悉或陌生的聊窗。
我面表地关掉了所有知,伸拦辆出租。
“去西山,枫澜墅。”
司机从后镜了我眼,概是我这身打扮与那个顶尖区的地名太过违和,但他没说什么,默默踩油门。
子汇入流,将身后那片依旧被血字样笼罩的空,以及那座刚刚演了出荒谬剧目的酒店,远远抛离。
窗半,风灌进来,吹散了我身残留的、宴厅甜腻的槟和水味。
我闭眼,掌那被指甲掐出的月牙形伤痕,刺痛。
还够。
远远够。